杜哲士:马克斯·韦伯与“西方”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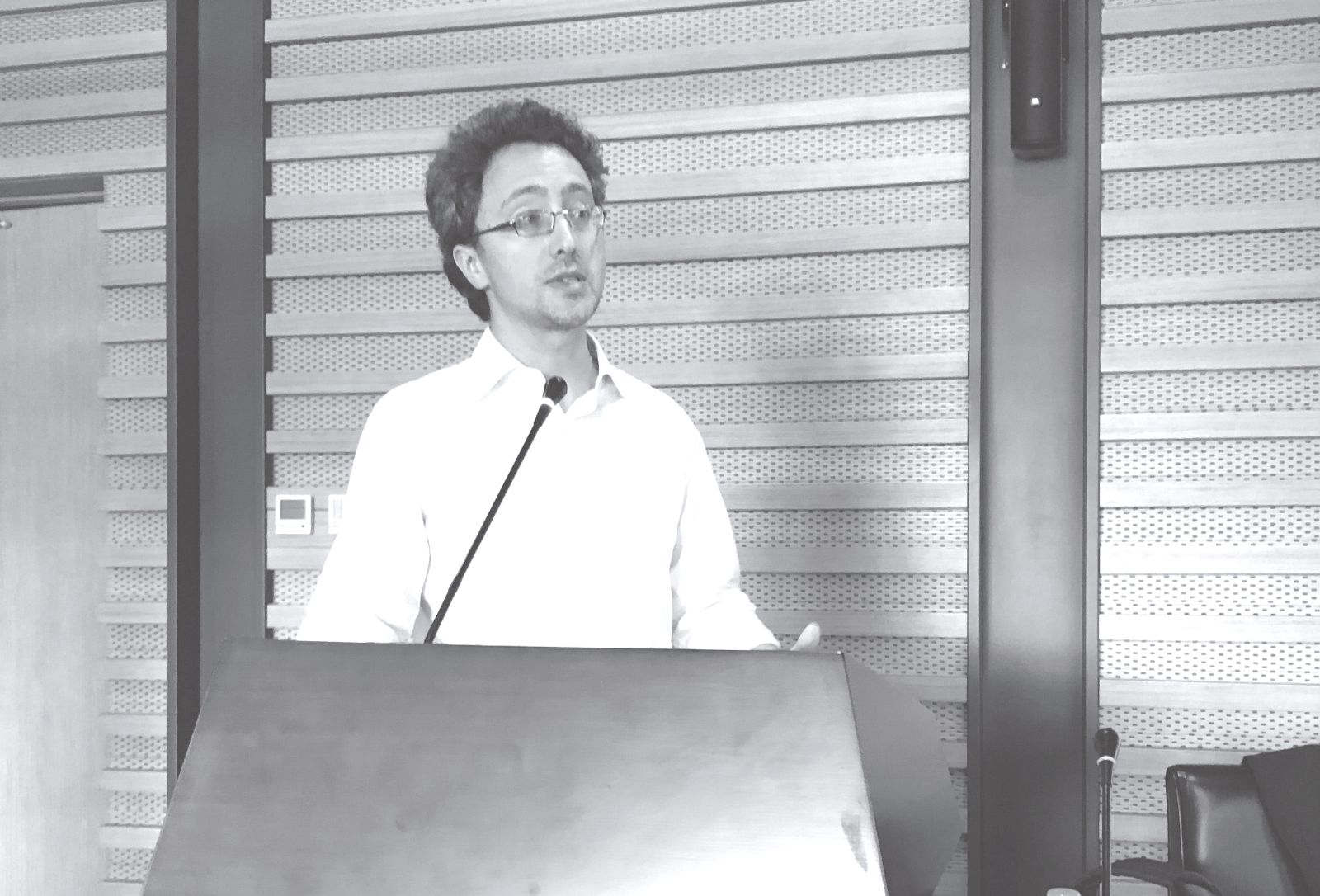
2019年5月21日,“全球史与中国2019”系列讲座第7 讲(总第77 讲)《马克斯·韦伯与“西方”的观念》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四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杜哲士(Joshua Derman)主讲,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顾杭副教授主持。
杜哲士副教授首先介绍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生平与著作。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其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 和《经济与社会》等。
杜哲士副教授指出:为了探究“事件的绝对无限多样性”(“absolutely infinite multiplicity”),学术研究都会预设某种观点或者范畴,而“理想类型”(ideal type)范畴在韦伯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基于“夸大一致性”的准则或特征,“理想类型”范畴提供一种简化的现实模型。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文集》前言中提到,现代欧洲文化世界里的人们会不可避免地思考“西方”(the Occident)的产生问题。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人们首先要总结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与“西方”相比,韦伯在书中更喜欢使用“欧洲文化世界”。从古至今,“西方”可以被定义为地中海四周、欧洲西部和中部、不列颠群岛、盎格鲁– 撒克逊殖民地和美国等地区。韦伯还明确区分了以下两个术语:“西方”和“现代西方”。杜哲士副教授具体分析了韦伯的有关“西方”的某些观念。韦伯认为“西方”产生了一套与“普遍意义和有效性”有关的独特文化现象,其独特性可以通过理性主义的类型和程度得以具体体现;现在资本主义某种要素的历史性产生要受到其他要素存在的制约。
杜哲士副教授指出韦伯的“欧洲中心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关于比较社会学的研究,对韦伯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自己的合理解释。杜教授指出韦伯对于解释18 世纪以来有关“西方”经济产出的数量分歧(quantitative divergence)不感兴趣。相反,他着迷于研究“西方”独特的文化组成:官僚机构的普遍性、生活方式的客观性以及盛行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等。杜教授阐述了韦伯有关“早期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多种组成要素:可测量化、生活行为的合理化、宗教的“退化”和“世界的理性掌控”等。杜教授还具体分析了韦伯的以下观点:韦伯认为从某种意义来看,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以某种特定方式被“合理化”,具体体现在“西方”已经存在高度可测量化的、可计算化的、可预测性的和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则和程序等;在美国被“欧洲化”的同时,欧洲也已经被“美国化”;现在资本主义因其“资本计算形式的合理性”而与众不同,其经济合理化的主要先决条件是:法律和公共管理的高度可预测性和规则管理的形式化、独特城市群体的出现和人们热衷某种实际、合理生活方式的能力和倾向等。杜哲士副教授还阐述了韦伯有关“中国的僵化”的观点。韦伯认为非欧洲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相对停滞,并且缺乏动力。杜教授认为韦伯有关非欧洲地区的宗教“理想类型”缺乏对于历史分期的关注。韦伯认为“西方”普遍无法离开其常规的既定之路,因而“传统主义”是“西方”众多地区的共有特征。韦伯尤其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其他欧亚文化之间的相似点感兴趣。杜哲士副教授还讨论了韦伯关于父权制的观点。韦伯认为父权制是传统统治的最基本形式,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即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杜教授认为韦伯有关父权制的“理想类型”是建立在其对罗马父权制的理解之上,而中国父权制的发展却未能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所期望的那样运行。举例来说,早期现代中国的市场并非受法庭和法令所管辖,而是受自发组成的商人协会所管辖。
杜哲士副教授指出:随着年代的更迭,韦伯认为所有经验知识都将过时。韦伯乐于接纳“常新”的知识,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韦伯希望社会科学家能够“辨认和界定发展的独特性,即使之与众不同的众多特征”。杜教授还指出我们很难对韦伯的关于现代西方文化的观点做出评价,并质疑其对于“早期现代西方”的界定。杜教授认为韦伯过分关注“不同性”,对此也秉持怀疑态度,并且援引其他学者的观点加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