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威教授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系列讲座十二讲
作者: 时间:2018年09月17日 00:00 点击数:
沈国威教授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系列讲座十二讲
2018年9月10日到9月13日,每天下午,都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四层报告厅听到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沈国威教授带来的精彩系列讲座,题为《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系列讲座十二讲》。此次讲座的主持人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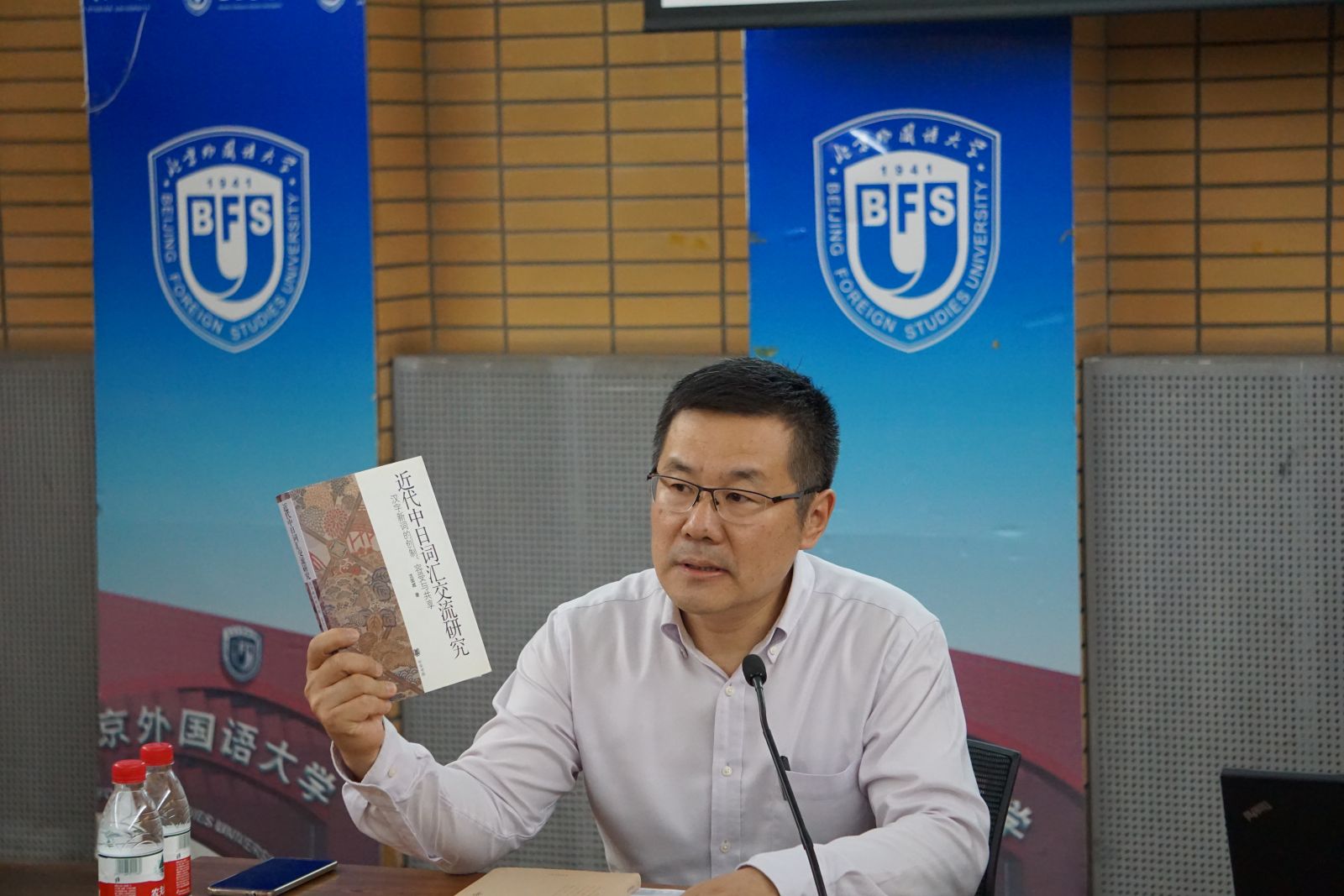
李雪涛教授主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系列讲座
沈教授研究“词汇史”,历史的视野在沈教授的讲座中贯穿始终。讲座首日,沈教授就对讲座题目中的“近代”这一术语,进行了词汇史意义上的梳理。此外,通过对“新汉语”、“新名词”、等概念的辨析,沈教授将研究重点定位到“近代新词”,即“汉语中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期间的新词。接着,沈教授从学术史的角度,以时序和国别鸟瞰了这一题目的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向我们介绍了近代词汇考源的文献资料和基本方法。尤为给人启发的是,沈教授对比辨析了“词汇史研究与概念史研究”两个进路:“词汇史研究的目的是词的发生、普及、定型以及汉字文化圈内的交流;而概念史研究其实是“东方容受西方概念之史”研究;两者的研究手法不同,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者之间更有小词与大词、文化史与文明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侧重和演进。”沈国威教授还特别举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来源日本及影响韩国的例子,来说明词汇在汉字文化圈的交互,更丝丝入扣地呼应了他的著作的副标题“汉字新词的创造、容受和共享”。
沈教授虽将目光聚焦于近代,却并没有放过对中日词汇早期接触这段历史的爬梳。重点介绍了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对日语的记录之后,沈教授带听众走进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的这段历史,以黄遵宪的著作为重点,阐述甲午战争之前日语词汇对汉语少有影响的现象及原因。
沈教授又分别考察了中日词汇大规模接触之前,中日因西方文明冲击共同出现的新词创制现象。一方面,17世纪初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在译书过程中创造译词,随着中国与欧洲交往加深,不同城市也出现了体现时代、地域特征的新词;另一方面,日本江户时代,译介荷兰书籍的“兰学”,在汉文是东亚唯一学术语言的情况下利用汉字创造译词。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又参考来华西方传教士的译文、遵循兰学的翻译原则来创造新译词。在这一部分,沈教授以1774年山田玄白所译《解题新书》为例介绍“兰学”是如何创制新词乃至新字的;以1881年井上哲次郎等编纂的《哲学字汇》为例说明明治时期创造译词时如何体现兰学的翻译原则。沈教授特别指出,“明治20年代”(即1890年代)进入了“术语完成期”:主要的英和辞典、术语手册初具规模;1891年近代国语辞典《言海》全卷刊行。

沈国威教授在讲座中
沈教授介绍,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日文新词一改过去对汉文的追崇;日文的汉文使用率逐渐降低,汉文教育也不再受重视。伴随着中日政治经济实力的消长,日语词大量涌入中国,一改甲午前死水一潭的局面,形成从东向西的巨流。通过翻译书、教科书、报刊杂志等方式;经由汉学家、浪人;吏、文化人、留学归国者等等,信息与知识从东瀛而来,日语也影响了汉语。沈教授指出,在甲午战败之前,中国译书以西文为主,但这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这一问题认识加深,认识到应该扩大译介西方书籍的广度、并加快速度。但西文人才不易培养,大量使用汉字的日语就进入了视野。沈教授以梁启超为样本,描绘了1895年前后先进知识分子对日本及日语的看法即转变过程。
在新词大量进入汉语的情况下,原有词典已然不能满足需要。1915年中国近代第一本国语词典《词源》出版。沈教授指出,此书“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新旧文化在语词上的冲突和竞争,”极具代表性。沈教授分析梳理此书收录的新词,特别对未标注词源的词的来源加以考证,体现出汉语正处于近代化的过程中。《词源》一书提示我们汉语出现了大量二字谓语词,沈教授指出这些词大部分都来自日语,形成的方式有三种:借形词、借义词、激活词。“借形词”是按照原来的词形从日语借入的词。“借义词”是,文字串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但是词义已不是原义,而是从日本借入的新义。也可以说词义的更新、扩大是在日本完成的。“日语激活词”是指在日语的影响下,某些汉籍词被激活,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一员。
最后一日的讲座上,沈国威教授慷慨地分享了他对近代词词源的研究方法。首先,深教授介绍了他研究使用的数据库以及相关文献。接着,沈教授用流程图的方式,介绍他是如何区分并定性借形词、借义词、激活词的。李雪涛教授做了精彩的总结发言之后,台下师生积极发言,分享自己的感想、启发、疑问,气氛热烈。为期四天的系列讲座在不舍的掌声中结束。
文/孟亚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