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ire of Tea》
史凯 译
20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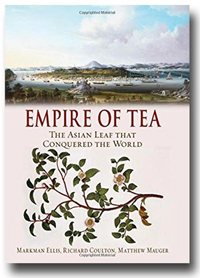
书名:Empire of Tea
副书名: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作者: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出版信息:Reaktion Books
页数:326
定价:£25.00
出版时间:2015-5
ISBN:9781780234403
茶叶进入英国人的生活已有四百年。从舶来的新鲜玩意到国内的居家饮品,从神奇的精神药品到随时“畅饮一杯”的优选,从社交礼仪的象征到一个人静思的伴侣,从专权垄断到国际品牌花样百出,从手工加工到工业化生产,茶叶的变身令人感叹。曾几何时,言说茶叶,必称中国。及至18世纪,茶叶又以英伦风范之貌示人。1863年伯明翰的一位杂货商异高呼“饮茶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卡逊民族与生俱来的嗜好”。后来,他的儿子创立了著名的茶叶品牌“泰福”(Typhoo)。茶叶一度属于精英的奢侈品,经过贸易和税收的推动,成为大众饮品。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还是政治经济、政府行为和国际关系的焦点所在。
历经变化的茶叶始终保持着最基本的属性:它出自一种特殊的植物(山茶科),由其树叶干燥制成。注入热水,即可饮用——这是一种神奇的饮品,人人唾手可取,却映射着宗教和阶级的差异。“下午茶”、“奶茶”、“晚茶”、袋泡茶与散茶、“建筑工人茶”(builders' tea)与格雷伯爵茶(Earl Grey)。一杯茶就是一份情(英语中有所谓“茶与同情”之说)。饮茶——与吸烟一样——既是自我体察的工具,也是参与社交的手段。
17世纪茶叶正式登陆欧洲,同一时期入欧的还有另两样饮品——咖啡与可可——三者的社会文化轨迹不尽相同,但共性也是明显的,欧洲人颇费周折才明辨区别。它们都是热饮(起初欧洲人并不习惯);它们都带着一种奇妙的苦涩的味道;它们可以调节精神,容易令人(或轻或重)上瘾。它们各自输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一点而非其中的化学成分,改变了饮用群体的文化。它们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咖啡原产于阿拉伯,可可原产于中美洲(Mesoamerica),茶原产于中国。它们的运输通道都伴随着暴力的阴影,也投射着新兴的经济结构。它们,三种苦涩的饮品,都需要加糖饮用——于是与奴隶制度产生交集。
这是一场宏大的历史叙事。“食物/ 饮品/ 调味品塑造现代社会”是当下的热门论题(包括盐、辣椒、玉米、鳕鱼、冷冻牛肉、层架养鸡、汉堡包),可惜坊间所见或流于肤浅,或言过其实,或荒诞不经。尽管如此,回溯食物的历史,复原流通的轨迹正应和着当下的大历史研究:长时程的历史进程,全球文化互动史,以及人类行为、客观事物和自然环境三者的关系史。以此而论,《茶叶帝国》是一例重要的研究个案。此书论述精妙,与西敏思(Sidney Mintz,1922— ,美国人类学家——译者)的经典著作《甜蜜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又译《饮食人类学:漫话餐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译者)相互辉映。两部大作都透过一种具体的消费品讲述现代性的历史。
17世纪欧洲人初遇茶叶。当时的产地仅中国和日本(中国的学生)两国。在华旅行者和商人接触到茶叶的基本知识。根据他们的记录,茶叶备受中国人推崇,其外观形状多样,特点价格各异;饮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流程周密细致,以茶具为核心,皇帝和朝臣无不沉醉在茶香中;中国人深信茶叶能够有效调节人的精神状态;茶是一种社交饮品,它可以兴奋大脑,活跃气氛。一些欧洲人深为茶的魅力折服:他们学着饮茶,一发不可收拾。还有一些欧洲人敏锐地捕捉到商机——无论经过陆路返回俄罗斯的车队还是荷兰和英国公司的商船,除了丝绸香料瓷器,都多了茶叶这种新商品。
中国茶,盛在瓷质茶壶里,缓缓倒入瓷质茶杯——这是英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茶叶源自东方的异质色彩已经被清除于他们的集体记忆之外。1650年咖啡和咖啡馆文化进入英国,一时引发广泛关注,然而最终胜出的是茶。不过,茶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并不简单,其间充满张力。
1660年塞缪尔· 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海军大臣——译者)这样记录首次饮茶的经历——“我从没喝过的一种中国饮料” ——不过最终他选择了咖啡。时隔几年,他说妻子遵医嘱饮茶治病——“佩林(Pelling)先生说,喝茶可以治疗她的感冒。”皇家医学院内部曾经展开激辩,争论的焦点是,那些新奇的热饮是否“适合我们英国人的身体”。茶叶的刺激和兴奋功效曾经招致一众医生和自然哲学家的坚决反对——威廉·巴肯(William Buchan,1729-1805,18世纪苏格兰名医——译者) 认为悲伤和肠胃气胀时不宜饮茶——不过专家们渐渐接受它的味道。尽管没有揭去毒品的标签,但茶叶的价值终于获得认可。这种“有益的毒品”可以控制癔病,抚平精神,宁静思想。
价格远在咖啡之上,这是它的不幸,却成就了它的地位。茶叶失去大众市场的份额,收获专卖的特权。皇宫侍臣与贵妇竞相追捧作为奢侈品的茶叶。今天你当然可以在一个挤满男人的嘈杂的咖啡馆里点一杯茶,但是18世纪初理所应当的饮茶场所就是私宅。上流社会女性的私人聚会上,茶是必不可少的角色,是有教养的社会上层的标志。典型的场景是这样的:“妈妈”亲手沏茶招待宾客。仆人从厨房取来热水,女主人取下挂在项链上的钥匙,打开茶叶罐的锁,把茶叶放入精美的茶壶,瓷质或银质的,注水,然后,逐一倒入客人的杯中(再加糖;1900年代之后多了牛奶)。茶具是最重要的一环。它们映射着时尚的历史,也为18 世纪欧洲的技术和商业进步提供直接驱动力。欧洲人需要大量精致坚固的瓷器,麦森(Meissen)、赛夫勒(Sèvres)、弓(Bow)等欧洲厂商相继破解了中国人的制瓷秘诀,这些公司烧制的瓷器可以承受高温,还能锁住茶叶的气味。
18世纪初的茶文化是社会时尚,也意味着女性气质,饮茶于是成为男性批判者眼中矫揉造作的靶子。他们斥责茶桌是“女人的王国,闲言碎语的源头,虚荣欺骗的工厂”。即便是约翰逊博士(Dr.Johnson,即《约翰逊字典》的编者塞缪尔· 约翰逊,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之一——译者)——尽管他本人酷爱喝茶——也认为喝茶这种社交活动可能沦为“扎堆胡扯的伪装”。“阴柔”的男性可能像女人一样喜欢搬弄是非。茶桌就是这样一个场所——人们喜欢它,因为友人在此相聚,人们非议它,因为流言蜚语在此诞生。
进入19世纪,茶叶褪去高冷的光环,走入寻常百姓家。恩格斯在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称,“在英国,甚至在爱尔兰,茶被看做一种极其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饮料,就像咖啡在我们德国一样。喝不起茶的,总是极端贫苦的人家。”一天供应两次茶饮被写进“标准女佣”的合同。主人离开了,佣人偷偷地尝一尝茶壶里剩下的残渣。茶配上粗颗粒的红糖,就是最初等的奢侈品。19世纪一个普通人收入的5%—20% 都用于购买这种“伤害性的麻醉剂”,还不包括烧水的燃料开支,慈善家和社会改革者对此忧心忡忡。
这种外来的东方饮品挤占了普通人食谱中的健康养分:他们本该吃面包配全麦啤酒。威廉· 科贝特(Willliam Cobbet,1763-1835,英国作家、记者——译者)批评茶叶是庸俗的奢侈品,只会消弱体质,腐蚀思想。“长期喝茶,体能下降,无法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渐渐毫无阳刚之气,变成缩在炉火旁边、赖在床上不起的娘娘腔,总之,染上懒散病,最后身体的病态彻底遮蔽了内心的愧疚。”茶可以轻易地“腐蚀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茶桌上的风言流语往往是风月寻欢的序曲”。任何一个理性之人都会“痛恨茶叶进入英格兰的日子”
居高位的权力者同样无法抗拒茶叶的魅力。1830年代之前茶叶进口贸易一直被东印度公司独揽。它还掌控着全球的中国茶叶买卖。茶叶运抵伦敦时要征收关税,转售给分销商时还要加税。政府希望从茶叶商品上获得足够的财政税收,但不希望税费过高影响茶叶消费,甚至催生走私。茶叶税的直接后果是,18世纪中期茶叶的零售价翻了一番。政府税务官前往各地清查商人的库存,审查他们的交易记录,收缴从法国、丹麦、瑞典和荷兰等地走私入境的茶叶,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东北部地区的措施尤其严厉。早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前很多年,就有大批茶叶从英格兰林肯郡的波士顿走私入境。它们最终流入伦敦市场,政府的财税损失惊人。
走私茶叶的价格优势突出,这不仅是逃税的结果,还与它们避开了中间环节直接面向零售商和消费者不无关系。彼时参与黑市交易的欧洲公司数量众多。茶叶走私贸易的规模令人咋舌:据信18世纪中期每年的交易额超过300万英镑。普通市民把走私商贩当做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却对缉私关员心怀不满。173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250名打击茶叶走私的官员遭遇人身攻击,其中6人遇害。政府不得不为偏远地区的缉私船配备武器,招募线人。在英国兰南部地区还公开处决一批茶叶走私贩。整个18世纪茶叶税问题都是政客之间相互讨伐的武器,即使北美殖民地上演了惊天变局,论战也未得消停。1740年代中期和1780年代,政府两次大幅降低茶叶税,茶叶走私终于得到有效遏制,消费量激增。
但是茶叶仍然必须从中国进口,而中国政府坚持要求以白银实物结算。重商主义一直批判英国人的饮茶嗜好,认为它是国库亏空的罪魁祸首。白银是中国对英国的唯一需求。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方案:设法调整对华贸易平衡,或者,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另辟茶叶来源。1770年代,英属印度半岛的植物园开始种植鸦片,那些所谓的“独立商人”收购鸦片销往中国,换回白银,平衡中英贸易。有良知的英国人为之不安。“如今的情形颇为吊诡”,1836年《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的一篇文章如是说,“我们在印度种植罂粟毒害中国人,得到的回报却是中国产的天然饮品,一种庶几为英国人专享的健康饮品。”鸦片进口激增,中国人终于有所警觉。皇帝下令禁止鸦片买卖,派人销毁数以百万磅计的鸦片。英方的回应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的枪炮外交。战争以两国间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作为结局,鸦片贸易继续进行,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双方付出的代价是,英方69条人命,中方,2万人。
第二种办法意味着新建一条英方控制的低成本的茶叶供应链。人们一度以为山茶科植物——这个名字出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aean)——只产于中国,但是1820年代英国人在印度南部的阿萨姆邦(Assam)发现一种茶树变种。它是茶树吗?它的叶子可以加工成中国茶那样的饮品吗?英国人在当地加工了一批茶叶,但伦敦市场反应平平。于是他们偷偷地从中国带回茶树苗和茶叶工人,尝试嫁接育种,未想大获成功,印度的茶树种植很快活跃起来。英国人迫不及待地宣称“欧洲科学技术……应用于茶叶生产的时机一旦成熟,中国茶叶将被远远甩在身后。”
印度的茶叶市场迅速崛起,国内环境资源和人口布局随之重组:丛林向茶园让路,各地大量招工,英国人意欲大力发展印度的茶叶生产,彻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1860年代,英国市场96%的茶叶来自中国,到了1903年衰减至10%,同期印度茶的比重上升到59%,另有31%来自锡兰岛。印度茶贴上了帝国茶的标签。对此,本书作者评论道,“归根结底,印度茶园让英国人实现了茶叶的英国化,最终建立起完全基于——而不是与之相对——英国本土商业传统的行业结构和运行方式。”这也是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41—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借《绿色的金子:茶叶帝国》( Green Gold: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 一书传达的观点:若非茶叶贸易,大英帝国和它的产业制度恐怕都无从谈起。
茶叶在英国早已告别高价,成为平价商品,这得益于诸多因素。铁路把茶叶直接运往印度港口(中国茶叶还得支付中间商一笔酬劳)。技术进步实现茶叶生产的工业化。其中,农业技术涉及单一作物的大规模生产、合理播种、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人力资源技术包括合理分配人工、新型的订单式生产和工厂化管理;设备创新也必不可少,英式茶杯的材质变化就是一例代表。1870年已经出现揉捻、切割和干燥茶叶的机器,此后,筛选、分类和打包设备相继问世。1910年代8000台机器彻底取代150万捻茶工。制茶的成本下降到机械化时代前的三分之一。
机械发明还改变了产品本身。机器氧化茶叶的效果更好,强化了红茶独特的味道。机械制茶产生的“碎茶”和“茶粉”杂糅在一起制成低价的混合品,英国消费者拿它们煮出浓香的饮品,用低成本享受高品位的生活。“泰福袋泡茶”的主要成分“不是手工卷制的茶树嫩叶,而是精加工过程的副产品”。碎茶和茶粉因其染色快的特点甚至身价倍增,这还要拜袋泡茶所赐——美国人在1903年的小发明从1950年代起成为英国市场的抢手货。
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还深刻地影响到市场销售。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带有商标名称的茶叶,它们配着私人或公司的承诺书,保证口感地道,然而品牌真正形成却是日后的故事,后发的印度茶叶尤其如此。19世纪实用科学和法律制度等新角色登上茶叶史的舞台。专家在法庭上面对议员提供真伪鉴定的证词。卖给穷人和美洲市场的茶叶掺着各种杂质(白蜡树、黑刺李、石墨、山楂叶、甘草等等),用“普鲁士蓝”(一种氰亚铁酸盐染料)、硫酸铁和红丹上色,甚至加入干燥的羊粪提高成色。1830年代税务署销毁了超过一百万磅的假冒“英式叶茶”(English leaf tea,指用发酵工艺制成的红茶——译者)——不过冰山一角而已。当时的新闻报道说,“方圆半英里都是黑刺李等仿冒品燃烧的味道”。造假乱象刺激着专业化发展——教人识别仿冒茶叶的手册指南和器具设备相继问世、相关的政策规定和法律措施陆续建立——当然,少不了品牌厂商信誓旦旦的承诺书。品牌化还意味着制造商努力追求口感的统一。专业鉴定人员的角色也大为强化。帝国、资本主义和现代政府的曲折历史与茶香的绵软历史交错在一起。
在本书结尾部分作者思考着茶叶的未来。传统的、英式的、散叶的、用茶壶泡制的茶叶前景喜忧参半。茶叶消费在日益富庶的印度次大陆呈增长态势,但在英国一路下滑。与此同时,咖啡消费——无论是速溶咖啡还是家中自制的私人咖啡——连创新高。有人把这种反差视为令人不安的全球美国化趋势的又一宗罪证——就像当年的袋泡茶一样。茶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而今却走向边缘化。茶党(tea party)一词21世纪的含义已经无关茶叶。今日美国市场消费的茶产品有85%属于冰茶,英国人饮用的冰茶也越多越多,放眼整个欧洲,冰茶消费量较之十年前已跃升两倍。
作者相信英式茶面临两个发展契机。第一,品鉴茶叶重新成为生活时尚。麦芽啤酒运动(Campaign for Real Ale,1970 年代由爱尔兰同名组织发起,反对大规模工业化和同质化生产啤酒,维护传统社会关系和消费者权益——译者)已经盛行多年,另一股热捧传统咖啡的潮流也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只愿接受天然种植、精心烘焙、专业调配的有机咖啡——苏门答腊咖啡豆——它气味浓郁口感醇厚,还带着些许无花果干的香气。两股热潮把传统饮品及其生活方式带回现代生活。英美两国已经出现茶叶复兴的迹象。经常可以见到未来一代的金融精英们品着顶级红茶操作苹果手机。另一个机遇要说到时下美国餐馆售卖的“热茶”。那是一个盒子,盛着袋装的草药混合物,有时甚至不含一片茶叶,味道颇为独特:肉桂味、香草味、杏味、苹果味、南瓜味。“红色能量”茶(Red Zinger,美国著名草本饮料品牌——译者)口味独特令人难忘,它是一种不含咖啡因和茶多酚的饮品,用薄荷、木槿、橘皮、玫瑰果、马鞭草、甘草、野樱桃树皮和柠檬草加工而成。早在18世纪,源自中文的茶叶一词就被移用指称英国国内的草本热饮。现如今浓香草本“茶”方兴未艾,这其实是又一例创新表象下的传统的回归。“茶”极有可能再次火遍全英,但这一次与当年“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毫无关系,未来或许是一个不见茶叶的“茶”的世界。
(史凯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