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文@吴礼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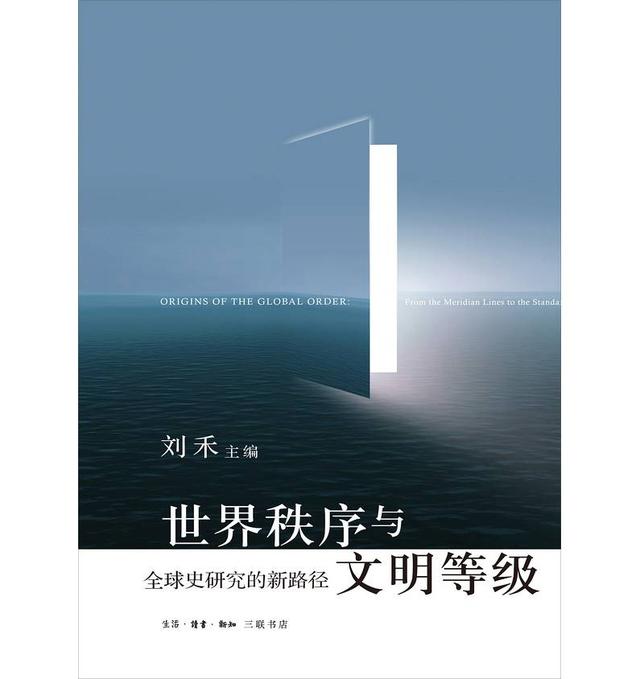
|
作者:刘禾(主编)
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名: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出版年份:2016
页数: 517
定价:58
装帧:平装
ISBN: 9787108055323
|
2016 年4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学者刘禾(Lydia H Liu)主编的论文集《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内收十一篇论文,分别从地理大发现、国际法、大同世界、世博会、语言等级等不同角度探讨“文明等级论”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对建构世界秩序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该书体例新颖、视角独特、材料多元,出版后在学界和读书界引发较大反响,《文艺争鸣》和《读书》杂志分别刊文予以评论、推介。
一
刘禾在序言中指出,我们今天的“世界秩序” 并非是“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而是肇始于1494 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签署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它在地球版图的意义上划分了这个世界的势力范围,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随着欧洲人创造的世界秩序向地球各个角落延伸,一个关乎“人心”的地缘政治——所谓的“文明等级”——也应运而生。 (第1 页)
这本书聚焦的“文明等级”,指的是从15 世纪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和世界文明等级标准的学说,它将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按照文明发展的程度划分为野蛮(the savage)、蒙昧(the barbarous)、半文明(the half-civilized)、文明(the civilized) 和开化(the enlightened)等不同等级,然后通过等级的划分建立起一套适合殖民统治的系统知识和思想秩序,如同一座森严的金字塔:文明和开化的国家居于顶端, 野蛮的国家位于底层,蒙昧和半文明的国家则夹在中间。(第7 页,第240-247 页)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变化,在19 世纪初形成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构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随着欧美的殖民版图和势力范围向世界各地延伸,文明等级的标准又扩散到全球不同地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实践。
总体来看,刘禾等人探讨的“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反映的是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和霸权体系在话语理论和实践层面建构、实施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我之所以说这本书体例新颖,是指它虽然是本论文集,众多作者却都紧紧围绕“文明等级论”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充分挖掘“文明论”这一话语体系的历史渊源及不同表现; 说它视角独特,是指它把“文明等级论”这套话语置于“全球史研究”的框架之下,强调“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促使人们去思考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深层问题;说它材料多元,是指这本书展现出的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多语言的综合水平,诚如刘禾所言,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研究范围则囊括学术建制、媒体技术、地球版图、视觉展示、科学技术、国际法以及形形色色的书写行为、翻译行为、学术行为。(第3 页)
二
如上所言,这本书的十一篇文章,都是围绕“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论”展开的,一方面论述现代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论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探讨“文明等级论”这种建构的知识在地球上的“空间”和“人心”两个层面的表现和影响。
唐晓峰在《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中指出,15 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其实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发现大量落后国族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由此逐步形成的文明——野蛮理论,依托新的全球地理观,将整个人文空间时间化、历史化,将空间差异整理为时间差异,即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文明, 由于其物质与体制上的一些不可否认的先进性,在其对野蛮进行干预、改造时便获得了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甚至被野蛮(未开化)的一方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唐晓峰谈到文明强国在处理边界问题时依据文明程度采用的不同手段:文明国家之间采用谈判和签署的方式协商边界;他们处理野蛮地区的边界问题时却采取简单粗暴的经纬线划分方式,根本无视当地的文化习俗;同时采用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来解决所谓半开化国家的边界问题。这种根据文明等级而区别对待的方式在刘禾的文章《国际法的思想谱系:从文野之分到全球统治》中有更深入地讨论。刘禾指出, 从19 世纪开始,“文明等级论”逐渐成为所有“主权国家”的共识。在现代国际法里,“主权国家”往往是“文明国家”的代名词,国际法即是文明国之间的交往法则,而文明国与“野蛮人”以及“半开化”民族之间的交往,采用是却是“国际法”之外的另一套规则:欧洲人对美洲、澳洲等地球上诸多“野蛮人” 的土地实施占领,乃是凭借“发现权”和“无主荒地”这一类概念来合法化的,而在对付所谓的“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亚洲人时,欧洲人则通常采用领土割让和治外法权的手段。这些手段在文明国之间从来不会使用,而半文明国家也从来不能向文明国家要求类似权利。
梁展的《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一文追溯了18 世纪以来西方政治地理学、人种学的知识/ 话语谱系,并以康有为《大同书》为例,揭示其建立在文明等级论之上的种族改良思想和实践所具有的虚假的必然性。梁展认为,“文明论”是西方世界为发动殖民战争、强迫其他国家开展殖民贸易而构建起来的、特殊的而非普遍和客观的知识形态。“文明”与“野蛮”,以及强调不同文明形态具有高下之分的“文明等级论”思想, 是这个知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它们逐渐形成了西方世界的地理学、民族学、人种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政治无意识”。“文明等级论”作为一种具有压迫性的知识/ 话语实践,反过来左右了并仍在左右着一些殖民地,或者那些曾经有过殖民地历史的国家里的知识分子关于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想象, 促使他们形成与此相应的改造自身文明和种族的思想和政治实践。梁展的这个论断,在赵京华的《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一文中得到相应的证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 完全接受并着力阐发文明、半开化、野蛮的三段式文明等级论,由此延展开“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而谋求国民个体和“一国之独立”的文明化预设方案, 从而有力推动了日本实施文明开化的各种政策。福泽谕吉的思想对晚清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的民权思想和“文明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样,源自欧洲的“文明等级论”,通过日本进入中国,成为这两个被称为“半文明国家”奋发图强的动力。
姜靖的《世博会:文明/ 野蛮的视觉呈现》一文,通过重温早期世博会中有色人种展览这一层面的实践,以及世博会模式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东渡过程中的复制与抵制,指出世博会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西方帝国主义及殖民扩张史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林林总总的世博会或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或以大众娱乐的形式,或以两者兼而有之的暧昧态度,为帝国主义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也为“文明等级论”提供了最为直观和生动的教学课堂。而宋少鹏在《“西洋镜”里的中国女性》中指出,欧美文明论中还有一个性别标准,即妇女地位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根据这个标准,野蛮人、蒙昧民族和半文明国家奴役女人,将她们视为奴隶,而文明国家和完全开化国家则将女性视为“同伴”,妇女受到广泛的礼遇和尊重。这一文明论中的性别标准在晚清通过传教士林乐知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传入中国,经历中国语境下的转化,对中国社会、中国妇女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文明论启动了中国的女权话语,使中国在文明标准的指导下展开女权实践。程巍的文章《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9 世纪发端于欧洲并在20 世纪席卷全球的思想主潮是民族主义,语言正是民族性的关键指标,而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在中国“最为通晓世界大势”的“汉字革命者”那里,这个民族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却被误判成“世界主义”演为“世界大潮”的时代,他们据此断言,中国人若不想继续“自外于世界”,要“做一个文明人”,只有毁弃本国的语言文字。因此已连续存在数千年而且本该成为中国现代统一国家心理认同基础的汉语,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突然变成了一个“问题”,这自然属于清末文字改革家和民国时期提倡“世界语”的知识分子的误判,而误判的原因,正是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文明等级论”:言文一致的拼音文字才是人类文字的最高形态,而汉语是一种“半野蛮的”、“原始的”文字,同时又是一种繁难的文字,若要绕过这个通往文明的障碍,就要将汉字字母化,或者干脆放弃汉语而使用世界语。“世博会”、“女权运动”和“汉字革命”,这些都是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热度的话题,若非经过上述论者的细致挖掘,我们很难发现它们竟然都和“文明等级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刘大先在《中国人类学话语与“他者”的历史演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西方早期人类学、民族学主张以现存的“未开化的”、“原始的”、“自然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带有浓郁殖民背景的话语被中国民族学者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并在实践中不自觉地将国内类似的边缘、边远、边疆族群作为对象。这套人类学话语本身构成了一套概念的牢笼,在中国学者将其本土化的过程中,很难摆脱既有的范式。从话语模式来看,“以自我为西方的他者”和“从自我中分解出他者”都缺乏自我反思的意义,因而在追求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将异文化归化了,忽略了被研究者的权益、情感和主体要求。既然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和知识体系带有浓郁的殖民背景,使用时很难摆脱掉它们既有的思维范式,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对于人类学这样完全来自西方的学科而言,一时很难回答,而对于植物学而言,孟悦的文章《反观“半文明”:中国植物知识的转轨与分流》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孟悦指出,作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一个门类,植物学在19-20 世纪是“文明等级论”生产的重要领域之一,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建立全球经济体系、把不同的历史走向纳入同一个普遍化的历史目的和未来图景的重要环节之一。西方的植物属种分类系统俨然成为大自然唯一的秩序和真实本身,是毋庸置疑的知识标准,而中国植物知识论在认识植物的种类名称上,如果不是野蛮状态,至少也处于“半文明”的进程中。孟悦将林奈的植物概念和吴其濬的植物概念作了细致的对比, 指出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即是他们对于生命体的不同理解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到了今天,林奈的植物体系可以说已经走入“历史终结”,植物猎手们采集的标本也只留下了图像,而吴其濬们对植物的体验却仍然是“活的”,不断打破光学显微镜和生化工业对知识的垄断,把生命的尊严归还动植物, 把声音、痛感、喜悦、生命的意识复归认识的主体。这是否说明源自“半文明”的知识体系自有其难以磨灭的价值,从而可以颠覆“文明等级论”的话语逻辑,还各种文明以其应有的地位和意义?
三
刘禾一直提倡跨语际的话语实践理论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2002 年, 她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译本由三联书店推出,该书即以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与英语、现代日语等其他语言接触、碰撞、融合后产生的书面形式变化,从而探讨自我和他者、历史、霸权、现代性、主体性、身份认同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她关注的是后发国家的现代性和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问题,而这自然会牵涉到知识和权力间的复杂关系。2009 年她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的话语政治》(The Clash of Empir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则聚焦于19 世纪晚期大清与英国间的“帝国碰撞”,以主权想象问题为中心,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她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帝国,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这本论文集延续了刘禾对话语、知识、权力的一贯关怀,因此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揭示出貌似客观的知识背后隐含的权力话语的运作机制。地理大发现之后,欧美殖民者根据一套“科学”的文明标准,把全球的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文明等级,然后理直气壮地推行殖民政策,这是知识上升为权力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文明等级论”化身为地理学、人种学、国际法、统计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先是以严谨的科学面目示人,然后又摇身一变,进入教科书当中,不知不觉地把这套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知识变成了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标准,从而内化了人们的思想, 规范着人们的行动。反过来看,殖民地的人民也逐渐接受并内化了这套文明标准,并未想着去质疑、突破和反抗它,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在这套等级序列里上升到和欧美列强同等的位置。日本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中国则紧随其后,其影响一直至于今天。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采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把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进行互动研究,这样中国的问题变成了世界的问题,而世界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问题,所以文集里的每篇文章都体现着对中国的现代性来源和身份问题的思考,如唐晓峰对中国人提出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的历史背景的考察;刘禾对晚清中国被迫施行的领土割让和治外法权在国际法层面的法理依据的探究;梁展对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种族改良思想和实践的分析;姜靖对中国人在世博会上被当成“低等民族”展览所作的追溯;宋少鹏对《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传入中国的分析等,无不是将晚清中国的各种话语实践放到“文明等级论”的框架中加以审视,以挖掘中国步入现代国家进程中
遭遇的各种屈辱、困难、抗争、变革和融合。
这就不得不谈到全球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问题。这里所谓的“出发点”,是指全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即从什么问题入手开展研究,而所谓的“归宿”,是指针对全球史研究的具体问题展开的思考和提供的解答。刘禾在《国际法的思想谱系》这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刘禾指出,她无意于在“文明等级论”的批判上做文章,因为这种非历史的价值判断,无法替代对话语实践的历史考察;她也无意于重新界定各种文明的高低等级,因为这样就会陷入“文明等级论”者设置的话语陷阱,从而被它有限的历史视野所误导。她的任务,是要对“文明等级论”的话语实践做出历史性或全球史的考察。换言之,刘禾这本书的问题意识即是要追溯现行世界秩序的来源和欧美“文明等级论”的建构过程。但是,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要求我们在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设想。跳出“文明等级论”的话语以后,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中重新展开交流和对话呢?刘禾在文章结尾虽然提出以人权话语作为一种替代的言说方式,但她也不禁慨叹,人权正在沦为新的意识形态武器,集结着新的权力对抗与角力。
此外,研究现代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论”这样充满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想要完全摈弃价值判断,对“文明等级论”的是非不置一词,又谈何容易!所以这本书虽然想用尽量客观的态度来揭示“文明等级论”的建构和现行世界秩序的来源,但字里行间均弥漫着对“文明等级论”的揭露和批判, 如刘禾对“发现权”、“无主荒地”、“领土割让”、“治外法权”等国际法外部“文野之分”理由的描述,姜靖论述“世博会”上中国人被作为“低劣民族”展出的经过等,虽然呈现的是客观的研究结果, 但从观点的铺陈和材料的选取来看,内中早已暗含作者的价值判断。自从历史研究变为一门学科以后,人们日益对它提出客观、严谨、科学的要求。但人文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变得像科学研究那样客观中立,甚至科学研究本身,究竟能否实现价值中立,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价值中立,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像后现代史学那样把历史记述仅当成一种叙事结构,那么叙述者又如何能够跳出自我的局限,获得一种全知全能、纯然客观的立场?
四
因此在我看来,这本书和很多后学著作一样, 最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可以启发人们对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提出批判性的反思。所谓“批判性的反思”,是指这种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明”的一面,而要将“文明”和“野蛮”并置,既要从“野蛮”的视角重新审视“文明”,也要从“文明”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野蛮”。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说,任何对文明的记录无不同时也是对野蛮的记录(There is no document of civilization which is not at the same time a document of barbarism)。本雅明的论断旨在反驳那些认为野蛮与文明是前后相续而不是同时存在的观点,这种观点属于进化论的历史观,本雅明一直不遗余力地与之对抗。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人类从野蛮中把文明夺取过来, 同时也是依靠了另一种野蛮(本质的暴力与支配) 才做到了这一点。野蛮,作为被掩盖起来的底面, 和文明如影随形,就像纸张的反面永远依附着正面, 悄无声息地打牢基础支撑起文明的滔滔雄辩,并且在结构上被排除在外以保证文明得以存在。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记录文明的史册进行X 光检查,以便揭露其中野蛮的痕迹,正是后者构成了前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它们回归到历史语境之中,而是要仔细地查看珍贵的文明成果,找出参与文明产生过程中的那些与匮乏、冲突、统治和巧取豪夺有关的叙事,本雅明把它命名为传统,指的是被剥削者的历史,它与胜利者的历史形成对比。从这一点来看,刘禾等人对“文明等级论”的追根溯源,在文化批判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长远的意义, 可以引发我们无尽的思考。
(吴礼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