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纪》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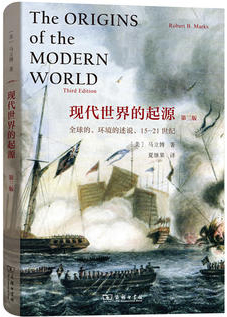 |
作者:[ 美] 马立博(Robert B. Marks)
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
书名: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纪
原作名: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译者:夏继果
出版年份:2017
页数:281
定价:62
装帧:精装
ISBN:9787100149945 |
| |
|
2015 年,南加利福尼亚惠蒂尔学院教授马立博出版了《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纪》第三版,距2002 年第一版出版已经过去了13 年。作者自陈其写作目的之一是撰写一本教材,可窥见其教科书的特征,它是各种全球史研究成果的综合—尤以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最为显著,而作者用本人的环境史研究将这些成果串联起来。最终,作者沿着时间的流向,绘制了一幅非欧洲中心论的、环境参与其中的人类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历史长卷。
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故事长久以来被以不同的方法讲述着。仅考察《现代世界的起源》这一题目,就不止马立博一家。如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本“中国特供”的著作却讲述了一个名为英国的主角发明了“现代性”并将之扩展到世界的故事。这种叙事可追溯到以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19 世纪欧洲社会学家。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称这种传统的叙事范式为“西方的兴起”,其情节如下:“现代性最初萌发于西欧,由那个时代和那个特殊地区的特殊原因所致;现代性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由欧洲人与其美国兄弟传播到全球。”他指出,这种叙述隐含的观点是,欧洲本身具有优越的特质;历史发展中欧洲占主动位置,其他地区是从动的—这就是“欧洲中心论”。
全球史逋一诞生,就主动承担了反欧洲中心论的任务。尽管全球史学家们一再小心,但仍然不免落入欧洲中心论或其他中心论的陷阱。全球史研究奠基人麦克尼尔的扛鼎之作《西方的兴起》将大量笔墨放在欧洲外文明的描述上,指出人类共同体漫长历史中,各文明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有其占优势的阶段,试图破除一种欧洲优越性“创世时”即存在的“神话”观。但当进入西方统治时代的叙事时(公元1500 年后),他却还是绘制出一幅欧洲主动辐射、其他地区被动接受的图纸。另外一些全球史著作则被质疑有陷入其他中心论的危险。和作者同属加州学派的彭慕兰、贡德·弗兰克就被评论家形容为介于“欧洲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之间。
如果说作者的全球史同行们在反欧洲中心论的论战中显得有些“宅心仁厚”,作者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则表现得“出手狠辣”,甚至“不留余地”。无论欧洲中心论者将“欧洲中心论”定位为“神话”、“意识形态”、还是败退到“理论”、“主导叙事”,作者都步步紧逼,指出其价值上的错误或逻辑上的缺陷。他“坚壁清野”:反对任何一种中心论,提出多中心论;反对“欧洲例外论”、“欧洲天然优越”观,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历史偶合”。同时,作者将这些特点渗透在其“述说”中。
如上所述,作者的叙事方式本身就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驳和颠覆。不同于传统以欧洲为范式的三段分期(古代、中世纪、近代),作者根据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将1800 年前的时代,统称为“旧生物体制”,这一时期,“人类维持生命和从事生产所需的能量,大部分来自于开发利用书木以及其他植物的生物质能”。在该体制下,一些农业帝国在人口数量、经济体量、文明成就上都较为成功,世界并非某一文明一家独大。尽管有辉煌灿烂,人类活动仍然受到该体制的限制,突出体现在可利用土地不足造成了人口上限的瓶颈。
作者认为,1800 年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欧能“摆脱旧生物体制的限制”,走向“人类世”,这一现象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是历史偶合的结果。作者这一理论,仿佛是历史学科的“量子论”,反驳着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是不掷骰子的”,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在作者的叙述中,哥伦布发现美洲首先就是一起偶然事件;天花瘟疫在西班牙征服美洲过程中起作用也具有偶然性。很多学者,包括麦克尼尔都将16 世纪视为西方统治时代之肇始,然而马立博将西方统治开始的时间大大推迟。他认为,虽然16 世纪后欧洲拥有了美洲、非洲广袤的殖民地,但19 世纪以前,欧洲比之亚洲仍不占优。支撑他观点的著作正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国因其特殊的银本位制对白银有着极大需求,而在新大陆发现以前,欧洲并无亚洲国家所需要的产品;新大陆上有着丰富的白银矿藏。这样,历史偶合发生了,欧洲得以大规模参与到印度洋贸易中。然而比之亚洲,欧洲在贸易上仍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为了“争夺在亚洲市场进行贸易的优先权”,内部产生了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欧洲的军事技术大幅度进步,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等领域也产生变化,催生了民族国家的一些特征。接着,多种力量偶合在一起,使得18 世纪英国在欧洲内部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英国在英法七年战争的胜利,再如比之稍早,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由于自身原因开始衰落,这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提供了便利。然而比之中国,这一时期英国仍然处于劣势。19 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局势,而工业革命同样是历史的偶合。作者的这一观点明显来自于彭慕兰的《大分流》,同时也结合了自己的环境史研究。作者是这样解释工业革命的:仔细考察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英国,就会发现传统上认为英国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因素“人口的推动与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并非没有,甚至比欧洲更为先进:首先,中国的农业生产实现了专门化、商业化,水路运输系统也保证了商品的快速流动;其次,中国也并非像马尔萨斯所认为的那样听任人口增长到农业发展水平的极限而不加控制,中国也有其控制人口的方法。但与英国不同的是,在上述中国的先进性、以及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走向了旧生物体制下生产能力的极致—“劳动力密集型和土地资源消耗型”农业,而不是走向工业革命之路。反观英国,与中国同样濒临旧生物体制的极限,本来也可能走上与中国类似的道路,但是英国幸运地拥有殖民地来提供工业生产原料以及食物,也以殖民地作为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开采成本极低的煤炭矿藏、以及重视煤炭开采的政府。这些因素的偶合,使得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产生。同样由于欧洲的内部竞争压力,英国人将工业革命的成果迅速投入军事工业,最终赢得了1842 年鸦片战争的胜利,天平从此向西方倾斜。18 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也标志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人类的行为能力一举压倒了自然的力量,全球人口大发式增长,人类从旧生物体制进入“ 人类世”。
工业革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它造成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在欧洲中心论的叙事中,这个故事蒙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成为“身处世界顶层的人们的自我安慰的意识形态” 。1900 年欧洲(及其北美后裔)已经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仿佛是由于欧洲种族天生就拥有智慧、勤劳等美德,是天生的强者。然而作者告诉我们,这不过是因为欧洲在一个“历史的偶合点”中得到支配其他地区的实力:首先,西方国家在竞争压力下纷纷谋求工业化,其结果是增强了整个西方侵略亚非国家的军事实力;其次,19 世纪70 年代在西方侵略高潮中出现了环境史上鲜有的厄尔尼诺现象,这造成的粮食歉收也使得亚非国家雪上加霜,西方却凭借对亚非国家的侵略渡过危机,双方差距进一步扩大。作者强调的是,既得利益者应该放弃洋洋自得的欧洲中心论,甚至应该感到庆幸和羞愧。
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人类世”已经行进两百年,前一百年的故事也告一段落,在本书第三版中,作者续写了后一百年的故事,即20 世纪至今。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第一、二版的副标题是《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在英文中,“生
态”(ecology)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自然,而“环境”(environment)则以人类为中心。作者也意识到前两版对人与自然关系交代得不足,第三版修订后增加了“环境”的内容,侧重于这种关系的改变对人类自身的影响。这些修订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新增章节“大转折”。同指工业革命,“大分流”形容的是对其产生原因的解释—英国与中国的“分道扬镳”,“大转折”则形容的是其后果—人与自然关系的扭转,人类的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自然。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作者对这种转折的思考也更为清醒:一二版的结论章划下一个问号“改变还是延续?”第三版则是笃定的回答“改变、延续及对未来的展望”:“人类世”的后一百年既是前一百年的“延续”,同时也是“改变”。“延续”的既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有着美国执牛耳的世界格局,还有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然而也存在着“改变”—人造活性氮、飞机、核能、计算机等技术“ 前一百年”的人类都闻所未闻,而亚洲国家的崛起预示着,未来可能进入亚洲主导的“亚洲世纪”。回到本书“安身立命”的环境,人类世中对化石能源的压榨,正如旧生物体制下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密集投入,或许未来同样会走向生态的界限,这些都值得我们警惕。
本书仍然留下几个问题。它虽然强调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传统关系不大,但是这种说法却对20 世纪新生的新化学工业、计算机技术、核能利用等方面解释力不强。此外,作者在解释南北差距增大的问题上,很多细节也显得语焉不详、缺乏对照,如解释差点沦为殖民地的日本,其快速工业化是由于其拥有一个“决心为建立强大的军队创造物质条件的强力国家”,却对奥斯曼帝国、中国、拉美、东南亚国家一笔带过。同样面对西方优势的形成,缘何日本迅速形成了力挽狂澜的“强力”政府,而其他国家政权江河日下,作者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总体上,这本书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作为全球史教材都非常优秀。它用三百页就提炼出人类六百年的历史,并了无痕迹地融合了全球史研究的众多成果。它的历史解释十分大胆,虽然对一些问题缺乏洞察,但可以作为未来激辩的出发点。
(孟亚琪)